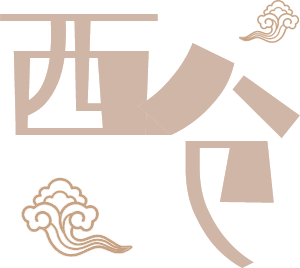


主笔:宁黛艳 图片:胡睿琳
古巷岑寂,墨蓝色天幕渐渐悬起,婵娟未沉,藏掖在老街繁茂的梧桐树梢若隐若现,晨霞送曙,唤醒历经百年沧桑巨变的西仓集市。
贾平凹在《废都》里是这样描写的:“那里是一个偌大的民间交易场所,主要营生是家养动物珍禽花鸟鱼虫,还包括器皿盛具,饲养辅品之类。赶场的男女老幼及闲人游皮趋之若鹜,挎包摇篮,户限为穿,几百米长的场地上人声鼎沸,熙熙攘攘,好一个热闹繁华。”
据史料记载,西仓曾是明清时期的官府粮仓,名为“永丰仓”,因与和平路的敬禄仓东西相对,故名“西仓”。清末时期,西仓作为官府粮仓,但职能有所减弱。又因旗人喜爱遛鸟、斗蛐蛐儿,当他们在西仓附近的校场军事操练时,跟班儿们便提着鸟笼、揣着蝈蝈儿筒在外等候,久而久之,周边巷道便渐渐形成以鸟虫为主的自由集市,西仓集市的雏形也就初步形成。旗人操练的校场设有栅栏,以阻挡闲杂人等入内,这道栅栏被称为“档子”,时间长了,逛西仓也被大家顺口说成“逛档子”。后来西仓的粮库改作军需仓库,平日街道人烟稀少,但每逢开市间,小商小贩们鱼贯而入,则是另一番热闹的景象。解放后西仓集市曾中断了一段时间,1978年以后逐渐恢复,并一直保持着逢周四、周日开市的传统,闻名遐迩的西仓集市延续至今。
熙熙攘攘闻声相往,摩肩接踵循迹而驰,斗转星移百年一瞬,找寻历史的脉络,从廪藏羡溢的粮仓、到戒备森严的军需仓库,再到如今演绎成喧嚣繁华的集市,坐落于莲湖区庙后街中段路北的西仓就这样静静蜗居在古都一隅,在现代感与怀旧风的碰撞中沉淀着老西安的鲜活百态与古朴气质。
这个春天,我们与古老的西仓相遇,一窥百年西仓中烟火氤氲的市井风情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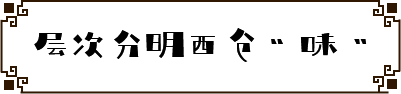
一蔬一饭,一饮一啄,皆是人间至味。晨起赶集,最要紧的第一件事就是填饱肚子。清晨5点,巷陌中的早餐铺就已升起蒸腾热气。在入口处先咥一碗咸香微麻、用料扎实的肉丸胡辣汤,浇一大勺油亮红润的油泼辣子,搭配一块麦香浓郁、韧劲儿十足的坨坨馍或腊牛肉夹馍,大快朵颐、满口噙香,食毕,微微发汗,美太太!开启元气满满的“逛档子”之旅。


逛吃逛吃,逛与吃总是形影不离,西仓集市集合了诸多坊上“忒色”名小吃,不需要依托宽敞明亮的店面,一辆辆简易的三轮车甚至小推车,车头插着简陋的招牌揽客,也能自如地发挥制作各式美食的小厨房功能,构成层次丰富、维度多元的西仓“味道”。清润甘甜的梨膏糖,焦脆酥嫩的炸丸子,溢香掉渣的油糊璇,滑溜爽口的麻酱凉皮,新鲜卤制的熟肉制品……没有一个食客会饿着肚子从集市返程。


除了熟食小吃,还有香气扑鼻的调料铺子,当天宰杀的牛羊鲜肉,物美价廉的时令蔬果……看似各不相干的食材辅料,在胸有成竹的家庭主厨眼中,一道道营养均衡、荤素搭配合理的精美菜肴早已呼之欲出。
西仓集市没有任何收费,许多菜农骑着自行车带上自家种的新鲜蔬菜到集市贩卖,挣多少得多少,既满足了附近居民的三餐所需,也让许多慕名前来“逛档子”的老饕们口福不浅,将春天的一口鲜味带回与家人共赏。经验丰富的阿姨们驰骋菜场多年,每人都有着自成一体的独家挑拣秘笈,总能不紧不慢的在一捆捆一堆堆的菜摊、果铺前挑选到最水灵最出挑的收入囊中。
汪曾祺在《家人闲坐,灯火可亲》中写道:“到了一个新地方,有人爱逛百货公司,有人爱逛书店,我宁可去逛逛菜市场。看看生鸡活鸭、新鲜水灵的瓜菜、彤红的辣椒,热热闹闹,挨挨挤挤,让人感到一种生之乐趣。”西仓“味”,便是这热气腾腾的生活滋味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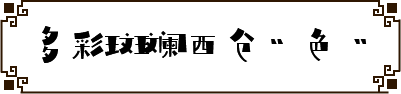
西仓共有4个巷名5条巷子,分别是西仓北巷、西仓西巷、西仓东巷和西仓南巷。最热闹的莫过于西仓北巷和东巷北段,那一带主要是花鸟虫鱼等聚集地,品类繁多、五花八门,天上飞的、水里游的、地上爬的……这里应有尽有。


如果西仓有颜色,那一定是五彩斑斓的。鸟市轻羽缤纷,各类品种、娇俏艳丽的鸟儿令人眼花缭乱;鱼市灵动明媚,摇曳生姿、悠然戏水的鱼儿让人心生欢喜;花草红绿相间,郁郁芊芊、花团锦簇的盆栽争奇斗艳;蛐蛐黑青紫黄,居于原木色或绿色塑料镂空的小圆盒里待人挑选……这些生机蓬勃、充满活力的小精灵们,是无数玩家的精神慰藉,也是大自然的原生态馈赠。自发形成的集市文化,也处处彰显着经济学的营销策略——与鸟、鱼形成互补商品关系的鸟食、鱼食、鸟笼、鱼缸景观等也是一应俱全。




谷雨已过夏将至,清晨的金色阳光温暖和煦,被巷子两旁的墨色树影剪碎,洒落在地面斑驳成白昼的璀璨星辰,置身于古老街巷的人们,或是拎着鸟笼驻足观赏,或是提着金鱼闲庭信步,或是手中盘着一对包浆的文玩核桃高谈阔论,短暂逃离都市生活的繁重压力,尽享“久在樊笼里,复得返自然”的片刻欢愉,赏鱼逗鸟的慢节奏生活给这里蒙上了一层复古的色彩滤镜,绘成一幅绚烂饱和、明艳动人的西仓集市图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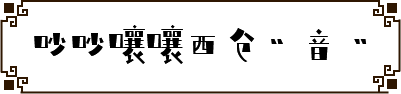
此起彼伏的叫卖声、你来我往的砍价声、婉转悦耳的鸟鸣声、窸窸窣窣的蛐蛐儿声、不绝于耳的车铃声、风吹树叶的沙沙声……繁忙集市的协奏曲,吵吵嚷嚷的西仓“音”,老西安民俗生活的市井风情极具治愈感。


穿梭在来来往往的人流当中,耳边充斥最多的,除了单口相声般带着扩音器卖力推销的“李佳琦式喊麦”,当属买家与卖家之间讨价还价的“battle”了。生活日杂、器皿盛具、古董旧物、旧书家具、民间偏方等,你想到想不到的,这里都有售,定价区间也随商品不同有着较大的跨度,不免有价格虚高的情况,“一定要还价”似乎已成为集市常客的行动自觉。“这建盏怎么卖?”“80元一个,这个纹路特别漂亮,尤其是倒上水之后。”老板娘边介绍边往盏中倒水,轻轻转动着向顾客展示日光下建盏底部的花纹变化。“太贵咧!便宜点吧,六六大顺,就66元卖我吧!”,“行吧,成交!您真会说话”。有意思的是,不同于火药味儿十足的争辩,这里的讨价还价更像是买家和卖家间轻松自然的攀谈,双方都乐在其中。即便什么都不买,遇上健谈外向的卖家,也会拉呱拉呱家常,谝谝闲传,别有一番趣味。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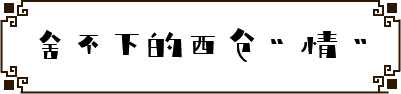
百年西仓,可谓是西安地域文化的“活化石”,是古城市井生活的缩影,更是老一辈割舍不下的情怀。放眼望去,来逛档子的多是中老年人。不熟悉网购操作的他们,可以在这里以相对低廉的价格,淘到各式各样的老花镜、镶牙补牙、拐杖拄棍等,也能较大概率碰上志趣相投的同道中人,互相交流养鸟养鱼、鉴赏古玩的心得,为平淡的退休生活增添几多情趣。



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引起了我们的注意,他独自静坐在路崖上,微蜷着双腿,与街上喧闹的人群形成鲜明的对比。老人手中握着刚从集市淘来的旧歌单,一笔一划认真抄录着上面的红歌曲目,时不时推一推稍稍下滑的老花镜架。“也是给自己找点事情做,我虽然经常来这边逛,但因为没有收入,我很少买东西,在这边抄抄歌单也挺知足的。”


“妈,您看这条好看吗?喜欢我就买了。”一位阿姨推着头发花白的老母亲在观赏鱼摊位前驻足,指着一条小金鱼俯身询问母亲。老人听力衰退,她扯着嗓子问了好几遍,又细心为老人整理戴好手套。集市拥堵异常,人行尚且不便,像她这样推着坐轮椅的老母亲出行,其中艰辛可以想见。也许小时候,是母亲带她逛西仓,长大后,换她带行动不便的母亲逛西仓。岁月的更迭从未停滞,曾在这里留下足迹的人逐渐老去,多年后定格成一张张泛黄的老照片,画面里的烟火气和人情味从未消减。
“我在这儿摆摊15年了”,花市一角的摊位前围满了人,热情爽朗的摊主乐呵呵地同围观的看客侃天侃地,身边环绕簇拥着生机盎然的各类绿植盆栽,“我就住在后面这栋楼,从小在这儿长大。”顺着他手指的方向,一栋极具年代感的老式居民楼在闹市中静默地伫立着。从咿呀学语到鬓角白霜,西仓陪伴了他的成长,他也见证了西仓的变迁,多年的练摊经历使他性格十分外放。“我的‘工作照’还上过电视哩,他们都夸我这儿取景好看,花丛中的小老汉哈哈哈!”说罢,引得众人开怀笑。在西仓,琐碎的日常也浸润着浪漫的诗意,摊主贩卖着一份人生的闲适,顾客采购着几许生活的温柔。

在都市霓虹的萦绕中,踟蹰在古老的西仓集市,指尖触碰墙上的一砖一瓦、足迹遍历那里的一街一巷,无不流淌着老西安热闹淳朴的氤氲情愫,折射出古都历史底蕴的厚重质感。董桥在《给后花园点灯》里写道:“不会怀旧的社会注定沉闷、堕落。没有文化乡愁的心注定是一口枯井。”西仓集市,渗透着无数西安乡党的朴素情怀。它的存续,让历史不仅仅存在于刻板的书卷之上,更让我们有机会与古人进行换位时空的对话,即便跨越百年,也牢牢维系着物理空间中千丝万缕的渊源。